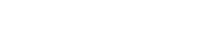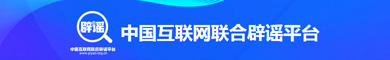時光深處有皂莢
外祖父的老屋前有一棵古老的皂角樹,樹干粗壯而斑駁,歲月在其表面刻下一道道深深的裂痕,枝葉繁茂如蓋,濃密的綠蔭灑下一片清涼。樹下,是外祖父教我讀書的地方,也是他和外祖母愛情故事的見證。
我的童年在皂角樹下生長成詩。盛夏的蟬鳴里,外祖父的藤椅總在樹蔭最濃處吱呀輕響。在樹蔭下翻開泛黃的書頁,“不必說碧綠的菜畦,光滑的石井欄,高大的皂莢樹……”他低沉而溫和的聲音,帶著歲月沉淀的韻味,將我引入魯迅筆下那充滿童趣的百草園。他布滿老繭的手指輕輕撫過文字,像是在撫摸時光的褶皺。每當我好奇地仰頭詢問,他便會笑著指向頭頂的皂角樹:“這就是皂莢樹,它見過你母親牙牙學語,也看著你蹣跚學步呢。”風過時,皂角莢相互碰撞,發出清脆聲響,像是時光深處傳來的遙遠應答。
外祖父教我讀書時,總是格外認真。他喜歡用手指輕輕劃過書頁上的文字,他的聲音不高,卻有著一種穿透力,每一個字都像是從心底發出的。他常常停下來,問我:“孩子,你知道‘皂莢樹’是什么嗎?”我會好奇地搖頭,他便會笑著指向頭頂那棵皂角樹,說,“這就是皂莢樹,它見證了我們的過去,也見證了你的成長。”我抬頭望著那棵皂角樹,樹上的皂角在風中輕輕搖晃,仿佛在回應外祖父的話,又似在與我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心靈交流,讓我感受到生命的延續與傳承。
外祖父會經常給我講書中的故事,他講得繪聲繪色,仿佛自己就是那個在百草園里捉蟋蟀、摘覆盆子的孩子。他告訴我,讀書不僅僅是認字,更是要理解文字背后的情感和故事。他常常問我:“你覺得魯迅先生寫這些故事的時候,心里在想什么呢?”我會歪著頭,認真地思考,然后小心翼翼地回答:“他是不是在懷念童年?”外祖父總是會笑著點頭,說:“沒錯,他是在懷念,也是在告訴我們,無論生活多么艱難,都要珍惜那些美好的時光。就像杜甫寫‘露從今夜白,月是故鄉明’,字里行間都是對故土的眷戀。記住,讀書是與前人對話,也是在叩問自己的心靈。”
那些饑荒歲月里,皂角樹成了生存的隱喻。自然災害的那三年,糧食短缺,生活困苦。皂角樹的果實雖然不能直接食用,但外祖母心靈手巧,她會將皂莢曬干,磨成粉末,再用少量的面粉和水攪拌,做成一種特殊的面團。有一次,外祖母帶著一小袋用皂莢做的面餅來到樹下。面餅薄薄的,散發著淡淡的皂莢香,邊緣微微泛著金黃。她小心翼翼地從布袋里掏出面餅,遞給外祖父。外祖父接過面餅,眼中閃過一絲心疼,他輕輕拍了拍外祖母的頭。那一刻,時間仿佛靜止,只有皂角樹的葉子在微風中輕輕搖曳,發出沙沙的響聲。
外祖父走的那天,皂莢樹無風自動,外祖母在樹下坐了整整一夜。我透過窗縫看見她的身影,像一尊被月光凝固的石像。第二天清晨,她照常起來搗皂角,只是那雙總是帶笑的眼睛,忽然添了許多化不開的霜。
“你外祖父說,這樹能遮陰、能結果。”外祖母把曬干的皂角收進陶罐,罐口蒙上粗布,用繩子扎緊,“他走的時候,還惦記著讓我留些皂角給你做毽子。”
我蹲在她腳邊,看她布滿老年斑的手在陶罐上摩挲。那些皂角被陽光曬得發亮,形狀各異,外祖母挑出一顆飽滿的,用錐子在頂端鉆個孔,穿進幾根彩色的雞毛,就成了我最愛的玩具。我在院子里踢毽子,皂角在鞋底輕輕晃動,偶爾裂開一道縫,露出里面褐色的籽,散發出淡淡的香。
“樹老了,人也老了。”外祖母撫摸著樹干上的疤痕,那是某年臺風過后,外祖父用布條裹住樹上的傷口,“這皂角啊,年年都結,就像有些事,總也忘不掉。”
如今皂角依舊,只是樹下的人換成了我。翻開《古文觀止》,忽然有皂角莢跌落在“庭有枇杷樹”的注腳處,恍惚看見兩個少年正從泛黃的書頁里探出頭來:都好好的啊。而他們的影子,永遠凝固在1961年的蟬鳴里。這時,風掠過皂莢,將這句叮嚀送往遠方……
樹影婆娑,時光仿佛倒流,那個充滿書香與溫情的童年,那些相濡以沫的歲月,都化作了永恒的記憶,在皂角樹下生根發芽,在我的心中永遠鮮活。正如李清照所說:“物是人非事事休,欲語淚先流。”但有些情感,有些記憶,永遠不會被歲月沖淡,反而會愈發醇厚,成為生命中最溫暖的慰藉。
□張昀
· 版權聲明 ·
①拂曉報社各媒體稿件和圖片,獨家授權拂曉新聞網發布,未經本網允許,不得轉載使用。獲授權轉載時務必注明來源及作者。
②本網轉載其他媒體稿件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。如因轉載的作品內容涉及您的版權或其它問題,請盡快與本網聯系,本網將依照國家相關法律法規作相應處理。


推薦閱讀
-
1市委理論學習中心組召開學習會議 06-06
-
22024年宿州市環境質量穩中向好 06-06
-
3宿州市2025年愛心護考活動啟動 06-05
-
4端午假期宿州消費市場“粽粽”日上 06-04
-
5
-
6市委常委會召開會議 06-0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