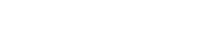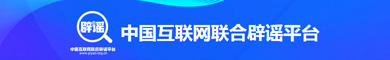家鄉又是高粱紅
20世紀70年代及之前,家鄉農村各生產隊人人都會種高粱,家鄉人叫它“小秫秫”。有“小秫秫”就有“大秫秫”,玉米就叫“大秫秫”。說來奇怪,若論個頭,這“大秫秫”反比“小秫秫”要矮上一截。
上世紀80年代開始,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,農民有了充分的生產自主權,種“小秫秫”的人家越來越少,而“大秫秫”大大擴張起來,再后來“小秫秫”幾乎沒人種了。近日下鄉,喜見有不少地塊呈現片片燦爛的紅霞,下車近前,才真切感受到那是高粱紅。
往事如煙,但記憶沒有抹去,把我拉回到半個世紀之前。家鄉農諺:“麥茬爛了頭,‘小秫秫’埋住牛。”那是仲春時節種下的“小秫秫”,出苗后嫩弱,經午季的干旱,一直長不高。“有錢難買5月旱,6月連雨吃飽飯。”一場透雨下過,“小秫秫”迅速上長,晚上若站在它的田旁,似乎能聽到它“咔嚓咔嚓”拔節生長的聲音。“青紗帳”就此形成。
“紅米飯,南瓜湯,挖野菜也當梁,餐餐味道香……”紅米飯就是高粱米飯。這首當年井岡山根據地紅軍唱的歌曲,飽含革命的樂觀主義,使紅軍戰勝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多次圍剿。其實,高粱籽粒無論煮飯吃,或做成各種飯食,滋味都比不上大米和小麥。但物質匱乏時期,它卻是貧苦人離不開的,這不單是因為它可以作為食物充饑,還因為它渾身是寶,從葉到秸稈到高粱穗下的莛子樣樣都大有用處。
三伏天是“打秫葉子”的時節,也是高粱地里最熬人的時候。日頭剛爬過樹梢,地里的潮氣就被曬成熱浪,大人們挽著褲腿鉆進高粱地,一手扶桿,一手往下扯葉,掰下的老葉子不能扔,要扎成捆背回家攤在場上,待曬得干硬,要么切碎了拌上糠料喂牛,要么扎成捆鋪在土坯房的屋頂,下雨時能擋擋漏下來的雨水,連屋檐下的雞窩,都能鋪上幾片防潮。家鄉農家人的日子,連一片高粱葉都要榨出實在的用處。可玉米就省心多了,葉子自始至終裹著桿子、棒子,不用人多碰一下。
“立秋三天遍地紅。”等到了白露,高粱穗子就紅透了,像一團團火把頂在桿子上,與晚霞相輝映成一幅唯美的畫圖。微風一吹,紅浪翻滾,連空氣中都飄著淡淡的高粱香。這時候,砍高粱的活計就來了。家鄉男人砍高粱,用的是頭彎磨得锃亮的小镢頭,雙腿叉開左手攬住幾根高粱,右手舉小镢頭,一根根左中右三下,“唰”地往上一拽,桿子就被整齊地一順頭放在地上,婦女則蹲在放倒的高粱稈上,用纏住布條的鐮刀片一一割下高粱穗。高粱穗要割到穗子一寸多以下,好等打下高粱米留做扎涮鍋的把子和各類笤帚使用。再往下的莛子,細細的、直直的,割下半米多長,那是農家做饃盤子、做箅列子等的好材料。
等高粱秸稈砍倒后,有的還發青,這是農家孩子解饞的時候,有的可以當成甘蔗嚼,還真有幾分甜味。這時地里的高粱稈要拾掇整齊,被捆成一捆捆豎在地里晾曬,等秫秸稈曬透了,再拉回生產隊分到每家每戶。這秸稈對農戶來說可大有作用,它可以扎成把子鋪在梁上蓋新房,也可截成段編成長長的籬笆,圍住院里的雞,也圈住家鄉人靠著高粱過日子的踏實勁。
冬閑時節,家鄉老人挑出粗細均勻的秫秸,坐在院子里老槐樹下,手拿篾刀,把它劈成細細的篾條,再浸上點水增加韌性,手指翻飛,不多時就能編出箅子、編出小籃子。若是編成長長的席子,夏天鋪上床上,比葦子席還涼快,躺上去能聞到淡淡的秸稈香,連蚊子都少來幾分。那時,農村青年男女新婚不少床上都鋪秫秸席,即使用葦席,巧手工匠還要用紅秫秸篾子在四角邊編上紅雙喜。冬天燒鍋時,抱一小捆秫秸塞進灶膛,“唰叭”幾聲就燒得旺,火苗映著灶臺的人影,也映著鍋里煮的紅高粱米粥。
家鄉又是高粱紅,為哪般?一打聽才知道,這每塊高粱地都是同高檔酒廠簽過約的。正巧碰上酒廠的技術人員來查驗,細問方知:高粱基本上是中國高檔白酒的基底,不論是茅臺、五糧液還是汾酒、古井貢、口子窖都是用高粱作為主要原料,它是常見的糧食作物蛋白質含量較低的,少了蛋白質的干擾,用來釀酒就最適合。此外,它的籽粒中含有大量單寧,會轉化為兒茶素、香草醛、阿魏酸等香氣物質,使高粱酒擁有特殊的香氣口感。如今家鄉的紅高粱給人們增加了幾分“醉”美,也能登上大雅之堂,走進詩與遠方。
□張炳輝
· 版權聲明 ·
①拂曉報社各媒體稿件和圖片,獨家授權拂曉新聞網發布,未經本網允許,不得轉載使用。獲授權轉載時務必注明來源及作者。
②本網轉載其他媒體稿件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。如因轉載的作品內容涉及您的版權或其它問題,請盡快與本網聯系,本網將依照國家相關法律法規作相應處理。


推薦閱讀
-
1市委理論學習中心組舉行學習會議 10-11
-
2任東調研技改投資項目建設工作 10-11
-
3宿州市秋糧收獲過半 10-11
-
4
-
5為譜寫中國式現代化宿州新篇章貢獻科技力量 10-10
-
6“三公里”就業圈“圈”出便民幸福路 10-09